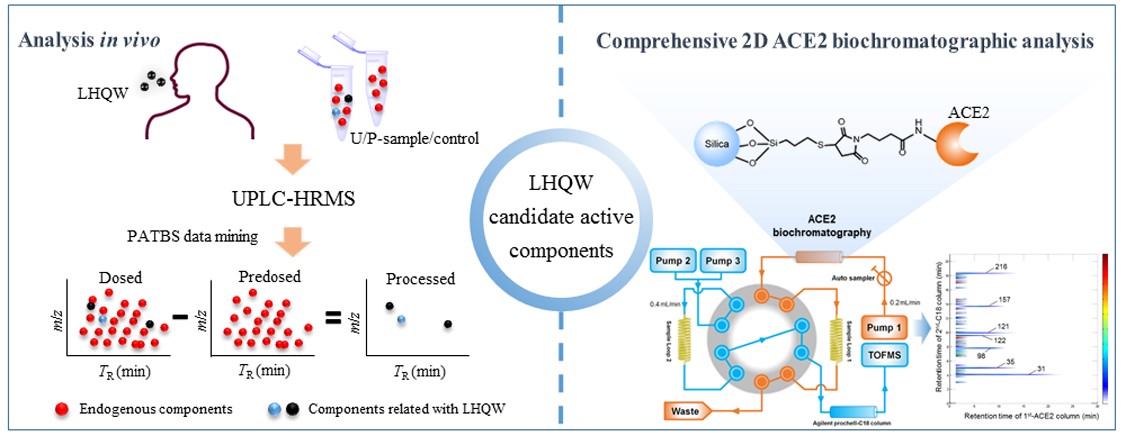你还记得“杀马特”吗?在这个热点急剧膨胀又飞快速朽的时代,十多年前的互联网话题,已经久远得像是上个世纪的传说,鲜有人再提及。
直到前不久,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引起热议。在纪录片中,李一凡撇去了故事线和我们想象中可能有的强视觉冲击画面,而是让一个个杀马特在镜头前讲述了各自迥异却又相似的经历。
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这些曾被主流鄙夷、嘲讽的杀马特们,一直默默在工厂流水线下挣扎生活着。身体是他们唯一能够反抗和改变的场域,外形则是他们的保护壳和安慰。
杀马特我爱你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虽然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但因为“回音壁”(echo chamber)效应,我们可能反而更难接触到不同圈层的人。或者说,更不愿意去了解那些标签化背后的真实个体。
如果说从“视觉系”到“杀马特”是一种文化下沉,那么,当互联网也“下沉”到小城镇和乡村时,如同曾经对杀马特的鄙夷一样,乡村身份在互联网上的出现以及某种风潮的形成,也引来了同样的嘲讽。
2016年前后,“乡村快手主播”进入了互联网主流视野,但很快就被视为“浮夸”“猎奇”的代表。直到2018年,社交网络再次被《当你觉得生活又苦又累时,去看看快手吧!》一文刷屏,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还有电工、司机、渔民……这么多在乡村生活的人们,在短视频里分享着自己的生活日常。
经历几轮互联网热议和讨论过后,即使我们试图带着善意和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主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善意多少都带着一些漠然和疏离。
这些乡村快手主播,在我们心中往往只简化为一个个乡村图景的显示屏。我们可能很少去思索,这些镜头后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直播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乡村日常,又为何可以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01.“一个苹果熟了,另外一个苹果又熟了”
“贫困家的孩子是否可以追求梦想”,一直是个沉重而难以回答的问题。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的答案。
故事还要从十年前说起,2011年,一位名为刘烨龙的年轻人来到四川大凉山支教。他本想待个一两年,就回家考个工作,过安稳的人生。刘烨龙没想到,10年过去了,自己依然留在大凉山,也陪伴和见证了一支土生土长的彝族少年乐队的成长。
刘烨龙在大凉山美姑县的一所小学做助教老师,学生们都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这些孩子多半怕生、警惕、不与人交流,甚至有暴力倾向……老师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
直到一天,一个原本内向的女孩,在操场边唱起了彝族民歌,不少孩子都围坐过来;她唱的是想家的情感,阿妈的民歌让这些原本封闭自我的小孩们,也展现了内心的情感。
刘烨龙和其他老师,便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彝族音乐兴趣班。唱民歌的孩子们,逐渐变得阳光开朗、不再害怕陌生人。
后来,这些孩子甚至开始自发地排练和表演,也颇为有模有样。刘烨龙说,只要一站上舞台,孩子们就“成了全场最靓的仔,眼睛里都冒着星星”。
图片刘烨龙记录的金花成长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神色逐渐变得开朗而自信
再后来,孩子们跟着音乐老师学习乐理、和声,并组建了合唱团。2016年,合唱团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剧院,举办了专场音乐会;甚至还参加了央视的元宵晚会。
受到鼓舞,一些喜欢音乐的孩子也梦想着成为音乐老师,成为歌手,但现实从来不是传奇故事,剧情的发展很快急转直下。鲜有人会把孩子的梦想当真,孩子们的家人笃定地认为这种“兴趣班”“就是三天热度,图个新鲜劲”。
更难以反驳、或许也更伤人的说法是,作为贫困儿童,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找个安稳工作,“穷人家的孩子去追求什么梦想呢?”
2017年,升入初中后,合唱团分散了。不止没有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就连合唱也是一种奢望。初中学校管理很严苛,休息时间弹吉他是不被允许的,合唱团主唱之一的小乌力因为偷偷练琴写了检查。
一方面,灵感、旋律和歌词依然不断在这些孩子们的脑中迸发出来,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劝说孩子们和刘烨龙放弃虚无缥缈的音乐梦。
迷茫和犹疑中,不断有人退出,但也有人再回来,经过数次讨论和争吵,乐队最后固定为现在的6个人,并取名为“拾光者”。过程中,刘烨龙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简单替他们做出决定,而是尊重了他们的想法。他则作为“拾光者”乐队的指导老师,指导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拾光者”包含着许多期冀,既希望纪念大家在一起十年的光阴,也希望作为一束光,能把彝族的民歌传唱给更多的人听。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a32126kqqaj.html)
“城里面容不容得下我/大山又留不留得住我/我都不知道/但不管走到哪里/大山都是我们的家”,这是“拾光者”原创音乐《山里的娃》里的歌词要传递的惆怅。
追逐梦想过程仍然不易。现在孩子们白天上课,晚上则利用空闲时间在快手直播和唱歌,这不仅是他们获得更多关注的途径,也可以通过打赏赚一点学费,维持生活。他们也一边学习着吉他、钢琴、月琴等乐器,作曲填词,目前已经整理出六七首成型的歌曲。
故事描述未免平铺直叙,但如果你亲眼见到这些孩子,也一定会被他们身上的那种朝气、热情和对音乐的坚持与笃定所打动。一旦讲起自己的音乐故事,孩子们眼中闪起光来。他们平时在昆明上学,但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到老家,有意识搜集民歌。
彝族的民歌往往是在生活中随兴唱出来的,他们或是跟在家人身后,在山路上边走边唱,随时记录;有些老人放不开,他们就趁着饭桌上喝酒后打开话匣子的时机,引导着老人们把民歌唱出来。
关于未来,刘烨龙和孩子们计划,成立一个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它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也不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就要扎根在凉山,这样“既出得去又回得来”。
在这样的构想中,音乐可以是照进更多彝族少年们生命中的光。就像刘烨龙当年做的那样,艺术这种东西,也可以走进乡村孩子的生活里,陪伴着他们成长。山里的孩子以前没有资源,他们就可以把这种资源带回去。
回顾这十年的经历,刘烨龙十分感慨,他说,这就是“一个苹果熟了,另外一个苹果又熟了”的故事。
02.“我与外面的距离被拉近了”
确实,走出大山,从来不是一条单向的路。
26岁的刘佳宁,出生于吉林舒兰长安村,她家周围,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山脉,一座又一座的高山。
大学毕业后,像许多东北离乡的年轻人一样,她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在传统观念里令人艳羡的国企工作。2019年,因为母亲的一次生病,她决定辞职回到家乡。
她刚回家时,周围的乡亲们十分不解,觉得她从一个成功走出去的山里娃又变回成了山里娃,大学就跟“白念了似的”,这让回到家里的刘佳宁也有些迷茫。
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刘佳宁对快手并不感兴趣。回到家后,她想着可以试试,就开了个快手直播。刘佳宁给自己起了个“森林姑娘”的ID,每天就直播着山区人在森林里的生活,上山下河、抓鱼抓雪蛤。
她点赞数最高的一个视频,是一位长白山采松人,蹭蹭爬上了几十米高的树丛。长白山的野生红松往往树干高大,松针茂密。因为需要爬几十米高的树干,采松人每次上树前都会买好保险,摔下来可能会重伤甚至丧命。
从记事起,刘佳宁就听说过好几起因采松丧命的故事了,“虽然有保险,但也是一条人命没了,一个家庭可能就此毁了。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尤其像我们林区,气温低,所有的资源收入都是来自于森林,采松籽、采药材、上山采野菜,养林蛙(雪蛤)。”
除了动作惊险的采松人,养蛙人则需要在冬天结冰时伸手进河里翻找林蛙,河水刺骨冰凉,时间久了,养蛙人的手部、腿部的关节处都因受冷而粗大。“其实农村人都挺不容易的”,刘佳宁叹气说道。
在她拍摄的老家视频里,其他出镜的人,全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这背后还是那个问题,东北大多数的农村年轻人几乎全数离开,现在留下的大多都是留守儿童,或是本身不太适合外出打工的人。
刘佳宁发现,手机镜头为乡村日常赋予了新的意义,生活日常的记录成了网友眼中的充满人情味的向往生活。
快手昵称/森林姑娘【户外】、快手昵称/原始森林是我家
也是通过快手,刘佳宁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同样在快手上直播森林生活的吴迪。吴迪家离她家不远,都住在长白山脉里,与她从城市回到家乡不一样,吴迪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
吴迪上初中时,父亲务农不慎腿部受伤,他选择辍学回家留在大山里,分担家里的农活。他每天走30多里的山路去森林里看护家里的几头牛,路上采些山珍,也爬过几十米高的松树采松子。
带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吴迪回忆,“以前我对外面的世界信息和认知全部来源于电视,2016年姨家的哥哥给了我一台他用了三年的智能手机,我像得到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注册了微信号,以前只是在电视上听说这些,既熟悉又陌生。
有一天在浏览朋友圈的时候发现一条有趣的视频,于是我下载注册了快手号,发现里面有好多新奇的内容,还能看到别人的生活,我还看到了跟我一样上山采蘑菇的视频,感觉好亲切,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真的好近,我与外面世界的距离被拉近了。”
吴迪也试着把自己平时的生活拍成快手视频,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直播时一下进来了几十个人互动评论,把他高兴坏了。可是直播没多久,就没人互动说话了,他才发现是手机没流量欠费了。
后来,随着直播次数的增加,吴迪的粉丝慢慢从一万,两万,涨到了几十万。他发现,来看直播的许多都是背井离乡的东北人,他们对故土有留恋,怀念这样的生活却又无法回去。
靠着粉丝购买和多次带货直播,吴迪和刘佳宁,把周围人采摘的山货收成,售卖出去许多。周围很多邻居一年的收入因此增加了好几千块钱。“别看只有几千块,很多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刘佳宁和吴迪说道。
吴迪反复强调:“我感触特别深,我从一个默默无闻最底层的那种人,现在能得到好多人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村的这些老人,家家都有增收,他们也都知道了网络是个好东西,能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很多人说我没啥文化,小学毕业。但是没想到我成为了主播,能帮助村民,通过快手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了家族命运和身边这些人。”
谈及互联网的普及,我们使用的词汇,常常是冷冰冰的,带着些许阶级意味的“下沉”。
早已熟悉互联网的我们,很难再有这样的惊喜感。但当一个人眉飞色舞地在面前,毫不掩饰、赤诚地反复谈及自己生活的剧变时,“下沉”两字反而变成了一种傲慢的视角,更完全无法概括这种信息的心情。
我们不仅看到了技术对一些人生活真切的改变。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反思的,我们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喜好和审美,带着某种特殊的凝视视角,来看待这些快手主播。
但对一些人而言,短视频的确是他们的一条出路,甚至已经是谋生的救命稻草。单纯批评“土味”或是“浮夸”,或许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何不食肉糜”。
3.“他们不是不能表述,而是总被别人表诉”
“他们不是不能表述,而是总是被人表述”,在接受采访时,《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如是说。
像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犯的错误一样,李一凡原本对杀马特的一些行为有着刻板的想象;但在实际接触中,他发现自己那种旧有的预判在陌生领域,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失灵了。
李一凡反思,“你要非常耐心和认真地去倾听,他的话才有逻辑。当你不相信,它就是碎片。你要是想去指导人家,你就看不到(背后的合理性),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我很相信肉身体验,特别是跨阶级,跟你生命没有交叉或生活方式差得很远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眼神,有时候你看他的一双鞋,有时候是在之前随便聊聊天,都是很不一样的。”
快手昵称/小乌力·拾光者计划
以拾光者乐队的彝族少年孩子们为例,许多人太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孩子的想法都是不值一提的,按照现有通用的道路来走,对他们的未来是最好的。
但在大凉山支教十年的刘烨龙发现,乡村孩子的教育,不能只有文化知识,更需要有梦想,有艺术的陶冶、兴趣的挖掘,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他们在社会中生活下去。
这种说法并非空中楼阁,2011年,策展人左靖(安徽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和欧宁共同启动了“碧山计划”,试图通过让知识分子、艺术家、建筑师与农村居民共同协作,重新发掘乡村文化,避免农村被简化为旅游景点或是迅速地被城市吞噬。
此后陆陆续续有人批评这个计划的可笑。但在10年后,越来越多人承认,“碧山计划”做的更多是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今天有人鄙夷乡村,这么多人从乡村逃离出来,正是因为在城市化运动和士绅化的浪潮中,乡村自身的文化价值正在消失。
事实上,就像拾光者演唱的彝族山歌一样,许多民间歌谣艺术、“非遗文化”,本来就是从生活中来、有感而发歌唱生活的,它们讲四时、讲饮食、讲万物,比如西北的信天游,广西的对歌文化。
如果缺失了那个地方的风土,即使文化最好被“保护”下来,也可能只是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而丧失了它本来的生命力。
拾光者搜集、重新整理和创造的民间的山歌,音乐成为了这些贫困孩子的另一条出路。假如他们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这些从生活中精炼而来的艺术,也许会继续滋养着后来生长的孩子们。
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当越来越多扎根于本土的拾光者们出现时,在原有的基础上,将会蜕变出新的生活和文化,在那片土地上流传下去。
04.需要的不只是平和的视角,而是来自他们的讲述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或少数,“佤族岩龙”是一位云南边陲的佤族主播,他平时在热带雨林生活,路上捡一块蜂蜜(蜂巢)随口一吃是常有的生活。
快手昵称/佤族岩龙
一次偶然,他把吃蜂蜜的视频上传了快手,得到了许多点赞,岩龙便向当地老人学习了养蜂的技巧,在直播的过程中,随着范围越来越广,除了风物美食,他也开始去探寻自己周围古老的佤族建筑、民俗、文化,并了解得愈加深入,“我们佤族是直接从部落过渡到现代社会的”。
在积累了几十万粉丝之后,也有人建议岩龙可以多加一些有嘘头、花哨的节目设计,但岩龙拒绝了,他说自己还是单纯聚焦于佤族和佤文化。
像岩龙这样的快手乡村播主还有很多,比如在大山里自在跳舞的大叔“大山里的舞者”,比如坚持凉山传统衣物技艺制作的“藏彝走廊的阿牛阿呷”,再比如坚持修大材小用的机械的“李有财 神器发明”……
快手昵称/大山里的舞者
当然不可避免的,会有主播走捷径依赖算法产出大同小异的内容,也会有人用浮夸的内容搏人眼球,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也有千千万万过着乡村生活的人,在忠实记录着自己乡村版图的生活图景。
也因为这样的视频,也许能让两个遥远的人产生微妙的联系,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命运,也许可以改变某种行为、选择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不断影响更多人。
今天提到的主播,全部来自于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项目用户,比起那些粉丝动辄以千万计数的头部主播,这个项目扶持得更多是粉丝十几万、几十万的中小主播。项目所看重的,更多也还是对于乡村价值的传递,对于周围人群的连带帮扶;希望不只是一个人成,而是一群人能成。
一直以来,对于乡村的想象往往会落入二元的极端中,要么认为是贫瘠落后,要么认为是田园牧歌。本质上,这两种视角都属于刻板印象,因为它将“城市-乡村”置于了对立的场景,并认为二者是无法转化的,更忽视了在其中生活着的真实的个体,其实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因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能平和看待他们的视角,更加需要的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更多元的讲述方式。
参考资料:《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张淼,the Initium Media
作者:看理想编辑部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新化月报网报料热线:886 2395@qq.com